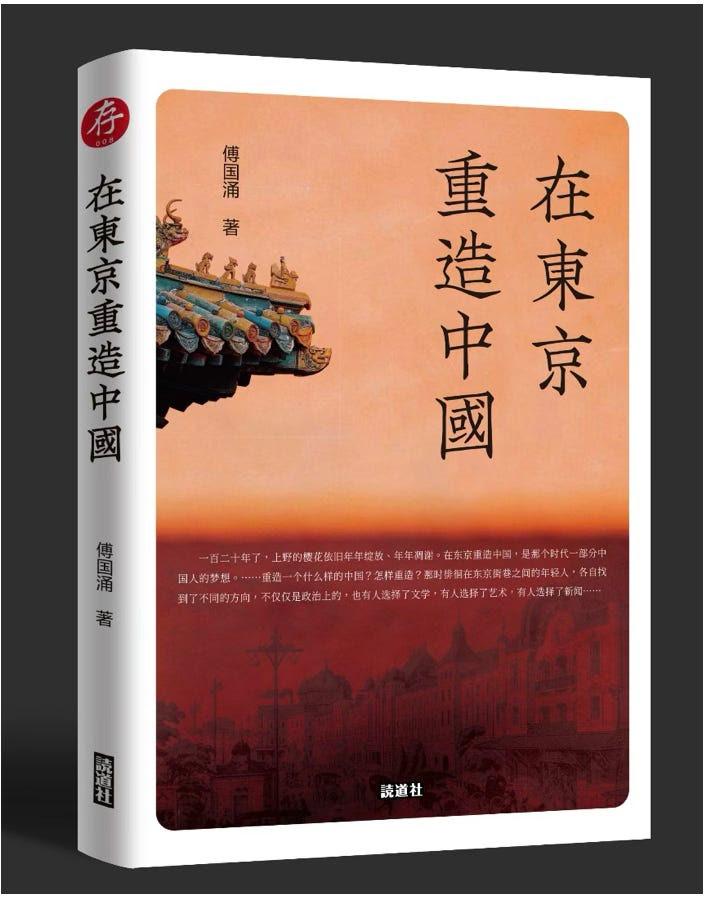
从1902年鲁迅、黄兴他们第一次来到东京,到民国诞生不足十年,从同盟会成立至此不过六年半,重造中国岂能如此轻而易举。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序言中这样说: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辛亥革命之后,试图在思想文化上重造中国的冲动也是在东京酝酿的。1914年4月,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最初是个月刊,针对袁世凯的统治,发表一些虎虎有生气的批评性言论。当时大有影响的记者黄远生“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的思路最初也是《甲寅》发表的一封来信。
同年7月,36岁的陈独秀第五次来到东京,在雅典娜法语学校学法文,那时他生活窘迫,穷得只有一件汗衫,上面爬满了虱子。他开始协助章士钊办《甲寅》。也因此结识了同为编辑的高一涵,和作者李大钊、易白沙,李大钊当时在早稻田大学留学。
正是《甲寅》直接推动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五四”的浪潮就是这样一浪一浪卷过来的。在东京的长夜翻译《域外小说集》无人问津的鲁迅,终于等来了他的时代,如何在精神上将一个古老民族带进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吃人血馒头的愚昧人群,有可能变成健全的国民吗?从东京开始的思考经过漫长岁月的酝酿、发芽,要长出枝叶来了。
那时候,中国的舞台上不仅有昔日东京的那些士官生,如今各地的都督、师长、旅长们,也不仅有国会里领薪水、举手投票的议员们,还有报馆的编辑记者、学校的老师,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做着不同的梦。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的展览说明中说,从事教育的最多,其中有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汤增璧。汤是江西人,与鲁迅同岁,也是南京选派的官费留学生。
《新青年》作者群中来自东京留学生仍是主流,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李大钊、高一涵、吴虞,只有少数像胡适这样的留美学生。
在教育部工作之余,北京绍兴会馆夜晚的灯光下,鲁迅将来自未庄、鲁镇的一个个卑微的小人物带到整个中文世界乃至域外操着各样语言的世界,人们不大会记得这就是当年在东京的那个年轻的周树人。此时,他在东京见过的同乡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范爱农们都已死了,见过太多死亡的鲁迅,他的目光是冷静的,他像一团裹着火的冰,给人冷冷的感觉。他在历史的缝隙里读出了“吃人”二字,他洞见了中国变革之艰难——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阿Q正传》从1921年12月4日到1922年2月12日在北京《晨报副镌》连载,而阿Q这个形象的灵感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鲁迅还在东京的那些日夜,他最爱看俄国作家果戈里的作品,还有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短篇小说。文学研究者韩南发现《阿Q正传》受到了显克微支《胜利者巴泰克》和《炭笔素描》这两个短篇的启发。巴泰克是一个最富自我欺骗天分的波兰农民,正是“精神胜利法”的典型。“正传”这个词也可能受了《炭笔素描》“正当的传记”(proper biographies)启发。(刘禾《语际书写》)
在共和时代即将被枪毙的阿Q 在供词上画押——
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 画圆不成,成了瓜子。这真是神来一笔。
民国了,但也不过是个招牌,只是剪了辫子而已。人民普遍不知共和为何物。民国初年,台湾人连横到大陆漫游,在一个茶馆里听两个人闲话,一个年轻一点的说:“前月公园开会,有人演说,谓今日为共和政体,我辈当知爱国,吾不知何谓共和?”老的说:“共和者,大家和气之谓也。我闻宣统皇帝年幼,不能亲理政事,命袁宫保代办,故我辈须和气也。”他们既不知道已是民国,也不知道袁世凯是总统,连横感到惊讶。
1906年,东京出版的《民报》第三号发表胡汉民执笔的《民报之六大主义》,第二个主义就是“建设共和政体”,“吾人信今日支那国民之程度,不可以无政府”,但是君主专制政体已不适合,20世纪要创设新的政体,必须抛弃专制,之前中国的革命最终都没有什么良好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改造政体,所以不仅要倾覆异族的政府,而且要结束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府。
同盟会在《革命方略》中指出:“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然而,何谓共和政体?直到民国诞生,举国上下,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
鲁迅在1925年6月16日完成的《杂忆》一文中带了一笔:“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
这年3月31日,他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这是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就在这个月12日,孙文在北京病故。第二天,《大阪朝日新闻》发表评论《孙文逝去——他的伟大唇舌之力》:
在日本,孙文拥有犬养毅、头山满等知己,对日本怀有强烈的憧憬,亡命日本时期更自称为中山,直到最近才改号为孙中山。虽然自诩革命家,其思想却带有极度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为了拯救陷入列强殖民地状态的支那,孙文总是不断地宣扬其思想。据说,孙文之所以能成为一号人物,靠的就是他那超乎常人的吹牛技巧。在支那,不论是政治家、书生、劳工,还是女人、小孩,众人并不称他为“孙文”或是“孙逸仙”,而是“孙大炮”,这个绰号才是他响彻全中国的大名。孙文得以当上首任大总统,可以说完完全全就是靠此“大炮”之功劳,凭藉其三寸不烂之舌,跌倒再爬起来,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成为伟大的英雄。(转【日】横山宏章《素颜孙文》,八旗文化2016年,5—6页)
从1895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在十六年的流亡岁月中,孙文往返日本十一次,累计停留了大约六年。进入民国之后,他又流亡日本,一共到过日本四次,停留了三年半。三十年来,他一共到过日本十五次,在这个岛国消磨了差不多九年半光阴。用他自己的话说:“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筹划也。”
岂止目不识丁的阿Q最后画了个瓜子,一辈子致力于革命的孙文也同样画圆不成,画成了瓜子模样。他离世之时,离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不到二十年,中华民国诞生已十四年,他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所以留下了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然他晚年选择与苏联合作,引入党在国上、建立党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将在他身后展开。
这一点就是鲁迅当时也没看明白。4月8日,他给许广平的私信中说:
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
国民性正是1902年他在东京弘文学院开始思考的问题,也围绕着他的一生,他致力于挖病根的工作。国民性能改造吗?如今已成为引起争议的话题。
直到1936年10月,他在上海病故,东京,关注着他的日本作家纷纷发表怀念文章,也有涉及他毕生对国民性的探究。增田涉回忆:
歌人柳原白莲君从日本到上海时,因为想会见中国的文学家,由内山完造先生的照应,邀请了鲁迅和郁达夫:在一个饭馆里见面,我也陪了席。那时,鲁迅很说了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坏话。白莲君便说,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他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那时我看见他的眼里湿润着。
那一天是1931年6月2日,鲁迅日记中写着:“晚内山君招饮于功德林,同席宫崎、柳原、山本、斋藤、加藤、增田、达夫、内山及其夫人。”达夫就是郁达夫,比鲁迅小十五岁,1913年到日本留学,在东京大学学的是经济学,却成了小说家。
眼眶湿润的鲁迅,对于他笔下的吕纬甫、魏连殳、孔乙己、祥林嫂、华老栓、阿Q、闰土……其实都有深深的怜悯,那是和他一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他们的命运和他的命运血肉相关。
如何让一个个不幸的生命获得正常的人的生活,他始终没有想明白,从东京到上海,他大半生都没有往制度方面想过,他和同时在东京、比他小一岁的宋教仁没有交集,宋所探索的那条路,他从来没有触及。所以,他也理解不了胡适他们1929年在《新月》杂志提出的人权、宪政问题。国民性的思考如果不进入保障人权的制度性探索,那也只能停留在文学的层面。这是他在东京没有启动的部分,也是一百二十多年来中国未曾完成的大题目——宋教仁之问,就是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专制土地上有没有可能实行宪政民主?《民报》与《新民丛报》争论的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
1926年11月又一个寂静的夜晚,鲁迅在厦门大学为杂文集《坟》写下一篇后记,里面收入的文章包括了他二十年前在东京写的几篇文言文。他以不无讽刺的口吻写下:“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作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他说的是实话,“筑台呢还在掘坑”?这是一个问题,不仅给他自己,也给我们这些后来者。
鲁迅之问是文学式的,是墨写的隐喻,不像宋教仁之问直接用血。如果说宋教仁是在筑台,鲁迅则致力于掘坑,前者从台上跌下来,用血浇灌了大地,后者只是想埋掉自己,化为大地上的养料。东京带给鲁迅和宋教仁的几乎是不一样的启迪,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他们能殊途同归吗?此刻,在东京郊外的一个角落里,我心中生出这个问号来。隔着差不多一百二十年的时光,今夜东京的月亮和他们看到过的还是同一个月亮。我想起宋教仁年轻的哭声,他无法知道身后铺开的历史之路,在他三十二岁不足的生命中,他已竭尽所能,并看见了帝国的落日,也看到了民国的曙光。
希望是什么?路是什么?鲁迅在《故乡》的结尾写了一句话:“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当他写下这些文字时,宋教仁被暗杀已快八年了。宋教仁的路没有走通,但在融入了他热血的土地上他所怀抱的希望灭绝了吗?
在宋教仁被暗杀一百一十多年后,其实我们仍在寻找真相,到底谁是幕后主使人?可以确定的是他想走的那条政治上和平竞争的路被逆转了,古老民族回到了以武力决胜负的路上。“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共和政体如何建设?他说,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国和地方的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都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的心思来研究。关于总统制和内阁制,他明确主张内阁制——
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
这是他1913年2月19日在上海的演讲,与他2月1日在武汉演讲时所说的“进而在朝”“退而在野”那番言论相呼应。此时,他所代表的国民党已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虽春寒料峭,他说这些话时却不无春风得意之感。3月18日,他告别上海前夕,在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上演讲,区别革命党与政党的异同,“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平和手段谋建设。今者吾党对于民国,欲排除原有之恶习惯,吸引文明之新空气,求达真正共和之目的,仍非奋健全之精神一致进行不可。”那一刻,他没有想到还要以自己的血来浇灌他参与创造的民国。
仅仅一天之后,他被子弹击中,再也来不及建设真正的共和政体了。
在东京的那些长夜里,他也曾灰心过,甚至流过泪,但他没有放弃,他相信破坏有期,建设有期。帝国向民国的转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易完成的。我想起鲁迅1925年在《灯下漫笔》中说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回到宋教仁,就是回到建设共和政体的起点上。在宋教仁来到东京一百二十年后的今天,与其问,宋教仁在哪里?不如问——宋教仁的后援力量在哪里?说到底,共和政体的支撑点是一个个争得了“人”的价格的人。